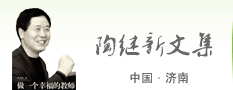“平”中见奇,“无”中生有
——薛法根老师的文化造诣与教学智慧
陶继新
小学语文教材中的一些课文,尤其是白话文课文与语言自然浅近的古诗,对于学生来说,并无多少文字障碍,有的也少语义蔽障。所以,有的老师认为这些课文言近意浅,并无奥妙,讲起来也就平淡无奇,学生听起来更是索然寡味。
其实,某些白话文古诗,尤其是名家之作,往往将言外之意、象外之旨,隐藏在看似平常的语句之中,“迷惑”了一般的老师,更“欺骗”了很多学生。
薛法根老师的高妙之处在于,他总能从“平”见出奇,从“无”中生有;并巧妙地引领学生走至那个美妙的境界。
为了让读者也去领略其教学风景之美与意蕴之深,笔者结合薛法根老师执教的几篇课文,为大家慢慢地道来。
(一)
《天游峰的扫路人》结尾有这样一段话:“老人朗声大笑。笑声惊动了竹林里的一对宿鸟,它们扑楞楞地飞了起来,又悄悄地落回原处。”学生粗粗一读,没有什么不明白的。但是,“飞起来”,却“又悄悄地落回原处”就显得很特别。一般写鸟被惊起之后,总会写它飞走了,而这里却写鸟又落回原处。如此一追问,学生顿时感觉此处写得并不寻常,熟知的文本立刻又了阅读的“距离”,而这种“距离”恰到好处地引发了学生对言语的推敲和揣摩:此处写宿鸟,其实是在写老人;宿鸟惊起又落回原处,因为它们离不开生活的这片竹林;老人早可以退休却仍在扫地,因为他离不开生活的这座大山。这样一想,学生豁然开朗。而仅仅这样理解和体会还不够,我进而追究:这里的“扑楞楞、悄悄地”等字眼还有什么特别的意味吗?读来让你有怎样的一种韵律与心绪?句段中的言语音韵之美、情意渲染之美,就在这样的“陌生化”中揭示得淋漓尽致。
《天游峰的扫路人》中只写了两个人物:一个是作者“我”,一个是天游峰的扫路人。两人虽有两次对话,但都是平淡如话。可正是在这种“平”中,却深藏着“奇”。薛法根老师不但有一双“平”中见奇的“慧眼”,而且引领着学生发现了其中的奇妙——
生:第一次是偶遇,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,所以仅仅写了老人的衣着和整体的大概印象:精瘦。第二次是惊讶之后的打量,所以将老人与众不同之处刻画得具体生动。
师:这个比较,我们清楚地知道了心境不同,所看到的人物的外貌也就不同。
生:我特别注意第二次描写,“瘦削、黝黑、炯炯有神”这些词语与第一次的“精瘦”形成照应。
师:你从语词上比较,很好!如果说前面是粗线勾勒,那后面就是——
生:工笔细描。
师:写人亦同绘画。其中的道理大概是相同的吧!
生:我感觉前后两次作者对老人的态度不同,第一次是萍水相逢的,(师插话:相识);第二次却是深入理解以后的相知了。其中的敬佩与惊讶之情隐含在这些词语里。
师:比如“黝黑”,有感情藏在里面吗?(生笑)
生:有!“黝黑”让人有一种健康、强壮的感觉,是一种健美,那就是一个赞美的词语。
生:“黝黑”常常形容人的肤色黑得发亮,黑得有精神,黑得有力量。我看到那些运动员的肤色就是黝黑黝黑的,不像我们白白的。(大笑)
师:如果换成“面色黑乎乎”的,或者“面色灰黑”——
生:(抢话)那就生病了呗!(大笑)
师:对老人的两次外貌描写,由外而内,由表及里,逐层展现老人的精神风貌,热情、爽朗、豁达、自信,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,既不显得很突然,又不显得很虚假。这,就是人物外貌描写的艺术。
通过这样一段教学实录片断,不但让我们发现了语言表层之下的精妙,也看到了学生那双“平”中见奇的眼睛。可是,如果没有薛根老师循循善诱的引导,也就很难有学生的这种发现。恰如中国第一篇教育学论著《学记》所言:“君子之教,喻也。”更重要的是,学生在他不断的诱导下,也就会形成自我发现文本内蕴的兴趣与能力。
除了上面被隐藏起来的“奇”之外,《天游峰的扫路人》还有一些人们未识的意义。比如为什么开始的时候写天游峰的险峻?为什么“我”是“终于”“顺着这根银丝上了峰顶”?足见一般人登上天游峰,该当何其难也!可这位七十来岁的老人,却是“每天早晨扫上山,傍晚扫下山”,而且还“轻轻松松,自在悠闲”地连说了两个“不累”。这除了说明他的身体健康之外,还有一个被隐蔽了的意义,那就是他太喜欢这个地方了。他已经退休了,本应在家安度晚年,享受天伦之乐了。可是,他却不舍得走。为什么?“喝的是雪花泉的水,吃的是自己种的大米和青菜,呼吸的是清爽的空气,而且还有花鸟作伴。”这说明,武夷山太美了!难道只是山水、花鸟等美吗?不!还有这里的人更美!老人如此,其他在这里的人都很幸福。而篇末所言“30年后”的对话,则拓展了生命的意义,让生命有了更高的境界。而这些,如果只从字面观,是不存在的;可是,我们却可以进行合乎情理的推进,发现“无”中之有。如果不对课文作深层次的探索,就很难发现其中的弦外之音、象外之旨。
其实,任何文本,都是有生命的人写的;教师教学的时候,不应当只是满足对于课文表面之义的了解,而应当走进文本之中,与文本作者进行生命对话,去触摸彼时彼地作者情感的脉搏跃动,进而去发现其独特的意蕴所在。
(二)
2012年4月20日上午,在杭州听薛法根老师执教的《雾凇》,颇为其“平”中见奇,“无”中生有而惊叹。
课文不长,可是,对于生于南方、长于南方的杭州孩子来说,真正领略其中的要义与美质并不容易。这些孩子到过雾凇“产地”吉林者寥寥无几,甚至一个也没有;雾凇在他们心里,只有一个虚幻的想象。可是,当听过薛法根老师执教的《雾凇》之后,雾凇则形象化地呈现在了孩子们的眼前,而且让他们对这个北方景观有了心向往之的游览欲求。
上课伊始,薛法根老师就让一个学生走上讲台,在黑板上书写“水汽、雾气、霜花、雾凇”四个词语。对于前三个词语,都是说的学生日常生活中所见的寻常之物,他们一点儿也不陌生。这样,无形之中,便拉近了学生生活与课文内容的距离。随后,薛法根老师便让学生辨识“水汽”“雾气”何以有的有“三点水”,有的没有“三点水”;而“雾凇”呢?又是两点水。这个时候,在一般人看来,他是教学生辨别疑难字。其实,从深层次上说,薛法根老师是不动声色地让学生初步了知了水汽、雾气与霜花、雾凇的内在联系。因为这四种景物都属于一个共同的物质,那就是水。没有水,形不成雾气;没有雾气,形不成霜花;没有霜花挂在树上,也就没有雾凇这一奇观的诞生。那么,前三个景物与雾凇之间到底构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?显然,在逻辑上构不成充分条件关系,而是一种必要条件关系,即“有之则未必然,无之则必不然”。不是吗?江南也有前三种景物,可是,江南却看不到雾凇。原因是,零下30摄氏度左右的气温,则是形成雾凇的必要条件的要素之一。这时候,学生就不是简单地知道了雾凇的概念,更重要的是,了解了雾凇形成的要件及过程。
这篇课文的题目是“雾凇”,可是,直接写雾凇的文字却非常少。这是不是游离了主旨?这当是一般读者生疑之处。解决这个问题,薛法根老师自有他的方法。他让学生进一步阅读课文,让他们从文字表层的“无”,去发现其背后的“有”。聪明的孩子经老师一点拨,于是,就发现了“白银”“银线”“银松雪柳”等词语了。这不是一般的水,也不是一般的雾,而是有着雾凇特质的物象。这些物象,可以让人浮想联翩,想见雾凇之美。
薛法根老师高人一手之处在于,他没有就此而止,而是又追问了一句:为什么用“白银”而不用“白糖”呢?它们都是很白的,而且白糖还可以吃呢。于是,学生七嘴八舌,说出了“白银很美”“太阳出来一照,闪闪发光”“为了突出更白”等答案。这已经相当不错了,可是,薛老师并不满足,而是在“银”上再加“砝码”。他说,白银是稀有的贵重之物,说到白银的时候,人们都有一种珍惜喜爱的感觉。这说明,不只是写它的白,还有作者喜爱的情感在里面。所以,读文还要读出作者彼时彼地的感情。所以,读的时候,要有感情地读。看来,作者之所以写雾凇,不仅因为它的景象美,还有一个重要元素,那就是作者对雾凇太爱了。王国维说:“一切景语皆情语也。”原来,作者之情并没有漂浮在景象的表面,当认真琢磨才发现,作者之情本然就“有”,只不过被作者悄然埋藏起来而已。
美仑美奂之物多不是一蹴而就便能形成的,雾凇亦然。据薛法根老师讲,在必要的条件具备之后,还需要8个多小时的时间,雾凇方才可能形成。那么,在哪些地方显现了这个漫长的过程呢?
这个问题,薛老师完全可以自问自答。他只是向学生抛出一个问题,由此激发学生的思考,并让他们透过文字,去体味这个过程的形成之美。于是,聪明的学生就找出了“渐渐地”“慢慢地”“轻轻地”等处于状语位置的几个词语。
薛老师并不满足,继续让学生寻找字里行间的“慢镜头”。于是,学生又找出了“一层又一层”。看来,雾凇的形成,不但需要一个过程,还有层层迭加的特点。不然,它就形成不了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绚丽景观了。
对于隐藏更深的“镀”字,学生并没有“发现”它的深义。薛法根老师则从化学方面进行了分析,说大凡镀者,都是金属镀也,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的。我认为,这里面还有两层含义:一是镀者,有镀银之想,镀银当是美妙之事;二是雾是在夜间“镀”成的,有神秘之感,可以启发人们神思天外,想象其独有的美妙。
看得出来,薛法根是一位很有智慧的老师,他不是将课文中的“平”中之“奇”与“无”中之“有”直白地告诉学生,而是引领学生一步一步地体会其中的要义。而且,他是那么地驾轻就熟,那么地从容自然。有的老师往往也试图引导学生探索文中之义,可是,故设的“痕迹”较重,少了水到渠成的感觉。任何教学,如果故弄玄虚替代了“道法自然”,再好的文章,也就失去了它本然的美丽;而教师,也就有了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的“嫌疑”。
(三)
白居易诗风浅近易懂,有“老妪能解”的传说。《夜雪》一诗,如果只观文字,亦无深奥难解之处。可是,细细品味,又觉其中诗意沛然,意蕴悠长。如果没有老师的相机诱导,小学生多难步入诗的意境之中。而薛法根老师,则巧妙地让学生从“无”中看到了有,从“平”中见到了奇。我们不妨看其中的一个教学片断——
师:夜雪,顾名思义,就是夜里下雪。当时诗人在哪儿呢?
生:诗人应该在窗前看着天上下雪,不然的话怎么知道夜里下雪了呢。
师:哦,诗人一直在等着看下雪?(众笑,生感觉有点不对。)
生:诗人在屋子里睡觉。夜深人静,谁会一直傻站着不睡觉啊?(众笑)
师:其实诗人在诗中清清楚楚地告诉了你,注意关键的字。
生:我知道诗人这时正在床上睡觉。“已讶衾枕冷”中的“衾”和“枕”是说作者正在被窝里睡觉呢!(赞叹声)
生:诗人正在被窝里睡觉,是被冻醒的。(众笑)“已讶衾枕冷”的“冷”就是告诉你,当时诗人的被子和枕头都是冷的,他是被冻醒的。因为我们睡觉时的被窝都是暖和的。(众又笑)
生:我补充,这还不是一般的冷,是冰冷冰冷的,“讶”就是冷得让人惊讶。
师:看来,同学们已经设身处地,像诗人那样地想,像诗人那样地生活了。(众笑)读诗就要体验作者当时的情境。那么,作者在被窝里睡觉,又怎么知道外面下雪了呢?
生:(争先恐后地)作者被冻醒了,连被子和枕头上都是冰冷的,就知道是下雪了。
师:雪夜寒气重,衾枕忽觉冷。这是从“触觉”上知道下雪了。
生:作者看到窗户亮起来了,就猜到是下雪了。
生:夜里漆黑一片,窗户照理是黑乎乎的。“复见窗户明”是说现在明亮起来了,那是雪光映到窗户上了,不是天亮时的亮光。
师:对呀,“雪光”映照在窗户上,泛出白色。这是从“视觉”上判断下雪了。
生:诗人是从竹子折断的声音中判断出下雪了。
师:哦?能不能说得更透彻些?
生:竹子上积了很多的雪就会折断,“时闻折竹声”,诗人不时地听到竹子折断的声音,就知道下雪了。
师:你能模仿一下“折竹”的声音吗?
生:“咯吱”
师:那是“竹枝”折断的声音。
生:“喀嚓”(众笑)
师:显然,折断的是竹稍,或者是整个竹子了。这是从“听觉”上知道下雪了。
生:诗人说“夜深知雪重”,这个“重”就是积雪压断了竹枝,发出清脆的声音,由此就知道下雪了。
生:雪积在松枝上的时候,感觉沉甸甸的。风一吹就一颤一颤的,好像很重的样子。(赞叹)
师:啊,你能凭借生活中的经验来体会这个“重”字,真会读书!这是从“知觉”上知道下雪了。诗人从“触觉、视觉、听觉、知觉”上判断出这是一场雪,那么,诗人知道这是一场小雪还是大雪呢?
生:(热烈讨论,略)
薛法根老师提出第一个问题“当时诗人在哪儿”时,多数学生还停留在诗的表层理解上,甚至误读了诗意。但他没有批评学生,也没有直接说出答案,而是很幽默地用了一个疑问句:“诗人一直在等着看下雪?”于是,学生恍然大悟。他依然不点破机关,让学生注意“关键字”。于是,学生便从“冷”与“讶”中,知道了这是由于下雪引起的。其后的两个提问“怎么知道外面下雪了?”“这是一场小雪还是大雪?”则引领学生走进了诗的深层意境之中。
对于课文中隐藏起来的要义,如果老师直接告诉学生,学生的记忆是不会深刻的,因为其思维向度没被打开,心情亦不兴奋之时,即使当时记下某些东西,也很难留在大脑的深层。薛法根老师的“道而弗牵,强而弗抑,开而弗达”,则让学生走进了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,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的审美境界,而且于不知不觉中人本悟到了白居易这首诗的妙趣。
当然,这节课的“平”中见奇,“无”中生有还不止于此,有些隐蔽得更深。如果不是对白居易其人其诗有所研究,是很难发现其“奇”其“有”的。鲁迅先生说得好:“我总以为倘要论文,最好是顾及全篇,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,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,这才较为确凿。要不然,是很轻易近乎说梦的。”读这首诗,我们当然也要了解白居易全人及其处所处的社会状态。有了这种思考,再一细想,“折竹声”于“夜深”而“时闻”,就不只是描写冬夜的寂静,还写出了诗人的彻夜无眠;还不只是“衾枕冷”,更透露出诗人穷困潦倒及谪居江州时心情的孤寂。
以上所谈,薛法根老师心知肚明,所以,他不仅引领学生感知诗人依次从触觉(冷)、视觉(明)、感觉(知)、听觉(闻)四个层次侧面描写的艺术手法,而且引领学生发现了诗中的“新大陆”。
评价薛法根老师的很多课,如果不对其全人及教学风格进行深入研究,也往往会步入“平”的误区之中。可真正走进薛法根老师的语言系统与思想殿堂之中,就会惊诧地发现,很多看似自然朴实的话语与平淡无奇的设计之中,都有他的匠心独运与出神入化之妙。之所以能够抵达如此之高的境界,不但需要深厚的文化功底,也需要超越常人的教学智慧。要想真正领悟这种大象无形之妙,不是仅从方法技巧上能够学来的,还要有情怀与境界。他是一位校长,工作之忙可想而知;可他一直站在小学语文讲台上,因为他爱学生爱教学如爱生命,他的每一堂课堂,都在与学生共同演绎生命的精彩。所以,才有了“平”中见奇、“无”中生有的生命张力。
薛法根校长简介

薛法根,现任江苏省苏州市盛泽实验小学校长,中学高级教师,小学语文特级教师。原创语文“组块教学”,主张“为发展言语智能而教”,2013年获得江苏省第二届基础教育成果特等奖。他的语文课“教得轻松、学得扎实”,形成了“清简、厚实、睿智”的教学风格,《卧薪尝胆》、《爱如茉莉》等经典课例深入人心。先后出版《为言语智能而教》、《薛法根教阅读》等5部专著,曾获全国模范教师、江苏省首届名教师、苏州市教育名家等荣誉称号。
(原载于《新教师》,2017年第4期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