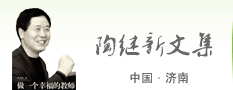莫高窟的痛思
陶继新
莫高窟俗称“千佛洞”,因其地原为莫高乡而得名,是一个世界级的佛教艺术石窟。因对佛教颇有兴趣,游览莫高窟,就成了我心仪已久的一个夙愿。中午到达敦煌市后,草草吃点午饭,便租一辆桑塔纳汽车,径向东南方向25公里的莫高窟驶去。
莫高窟开凿于鸣沙山东麓的峭壁上,坐西朝东,与三危山东西相望。它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,历经隋、唐、宋、元等11个朝代的不断修建,方才造就了以大乘佛教不同时期、不同宗派所崇尚的经典为根据的壁画和彩塑。它南北长1600多米,壁高50多米,现存洞窟492个,其内容涉及到佛藏中的经、律、论、史四大部分的绝大部分内容,构成了当今世界上保存较为完备的佛教美术馆与佛教图像宝窟。在其间听导游纵论古今,观形形色色的艺术珍品,恍若走进千年历史长河之中,与不同时代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艺术相触摸。
但是,莫高窟中的不少珍品,已经不在莫高窟,亦不在中国了。20世纪初,一些来自不同地区、不同国家的“探险家”“考古学家”“考察家”“游历者”,陆续向莫高窟进发。自1905年帝俄勃奥鲁切夫探险队盗走古经卷一批始,此后英国人斯坦因、法国人伯希和、日本人吉川小一郎、俄国人奥尔坦布鲁克、白俄陆军少校阿连阔夫、美国人华尔纳等,都不择手段地将这里的很多文献、文物盗运而去。
游览的人们,从大人到小孩,从男人到女人,无一不在痛骂这些外国人的强盗行径。骂是应该骂,但痛定思痛,似乎还有值得我们的先人自责的东西在,还有应该值得我们后人反思的东西在。上世纪20年代初的敦煌虽早已拥有了丝绸之路的昔日辉煌,但当时没有汽车,也没有公路。试图从外国到莫高窟,需跨越茫茫沙漠,往往是数千里见不到水,看不到人,甚至是与死神握手相见。来此盗宝,其险可知。今天我们从敦煌向莫高窟的路上,所见全是戈壁荒漠,除屈指可数的沙漠之草——骆驼刺之外,看不到任何的绿色。而听司机王启军先生讲,这对于整个戈壁滩而言,也只是冰山一角。当时外国人意欲进军此地,没有冒死而行的胆量和决心,没有随机而行的智慧与才能,只能是望洋兴叹或者客死异乡。那时中国不乏文化之人,也不乏勇敢之士,但他们大多不知道莫高窟,也不知道莫高窟的价值。这对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来说,无疑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讽刺。1909年法国人伯希和仅将盗走的少数经卷在北京展出,就震惊了中外。此时中国北京学部才于1910年命令甘肃当局将剩余残卷运至北京。起运时仅剩的8000卷经卷,又被王道士偷藏偷拿了一些卖给外国人;沿途又被各路官僚多方克扣。对此,余秋雨先生在他的《道士塔》一文中曾做过详尽的描述。
所以,游罢莫高窟,在我心中回荡的,多是屈辱与悲哀。勤劳、智慧的中国人民创造了伟大的石窟艺术,又被中国人拱手送给了外国人。被盗也罢,被骗也罢,被卖也罢,毕竟一去不复返了。目前,西方一些国家博物馆里,摆放着中国敦煌莫高窟的艺术珍品,引来一批又一批观览者的惊叹声。试想,我们的国人能有几个也赶到遥遥万里的外国,搞来一批批他国的艺术珍品?但有人会说:盗不可干,此为强盗之举;骗亦不可干,此系小人之为;买吧,高价尚可,低价就很难了,如法国人仅用一叠子银元就从王道士那里换取24大箱经卷、5箱织绢和绘画的买法,我们可干不了。再说,如此危险之地,如此遥远之路,如此行路之难,如此生命之忧,对于“珍爱生命”远远超过珍爱艺术的中国人来说,是大大不可为的。
智慧、勤劳、勇敢、文明的中国人,你究竟在哪里?
(《行旅有道》,陶继新 著, 2015年10月第1版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