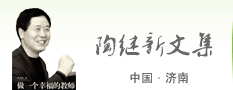蒙山的木道和夜景
陶继新
今天已是第三次登上蒙山,与前两次不同的是,这次夜宿山上,且独自行走了“天下第一木游道”。
以前登山,走至雨王庙与翠云观时,便认为到了旅游的最后一个景点,没有继续上行。这次下榻的蒙山会馆,就在雨王庙与翠云观之上百米左右。
窗外便是漫山的绿色,傍晚的秋风正在清爽地吹着。不能辜负了这天然的恩赐,于是尽快走出房间,到山林间去享受无处不在的清新空气。
出蒙山会馆西北方向而行,不远处便见一行木道蜿蜒西行而上。起端处立有一个木牌,上书“天下第一木游道”几个大字,下面便是简短的说明。说这一木道于2002年4月建成,由46000根2米长的红松圆木铺成,长达3990米。2004年8月申请基尼斯纪录,成为世界之最。
这令我顿感兴趣,因为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。喜欢登山,又对自然景色和奇特景观情有独钟的我,对这种原木制作而成的木道,就又多了几分好奇与感情。于是,决计在这个木道上一走为快。
太阳已被西边略高一些的山头挡住,只有那绚然的红色,还在西方温情地燃烧着。
踏着一个一个红松圆木铺就的道路西行而上,清凉宜人的山风不时在我的脸上抚摸复抚摸的时候,心里的爽快惬意也就无边无际地流淌回荡。路上一个游人也没有,目之所触,全是一尘不染的绿色。偶尔可见细细的清水,缓缓地悠然地流动着。鸟儿在山林中断断续续而又自得自乐地鸣唱着。舍此之外,除了我的有节奏的踏击木道的脚步声外,就全然归于静寂。
继续前行,除俯拾即是的绿色之外,还不时有些别样的景点,或悬崖,或佳木,或奇石。由于步步登高,此时的夕阳因没了山峰的阻隔已经呈示在我的视野里,与山林共同渲染着它那红绿相糅的壮观。
这时已经到了栖凤山上,一个木牌赫然而立,上面写着经中科院环境研究所测定,此处为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负离子含量最高的地方,含氧量为北京的195倍。
贪婪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,尽情地收拢着这分文不花的无价之气的遗赠。遗憾的是,更多的游人并不知道这一木道如此无声而又自然地延伸着,也不知道这里有着如此丰沛的天然氧气,更感受不到这种幽然而行的特殊美感。
不过,想来也并不奇怪。一是因为人们从山下登至雨王庙时,多是认为已经到了游览的尽头,继续上行不会再有更加奇异的景色。二是步行至此的人们多是当天上下,犹如“强弩之末,势不能穿鲁缟者也”,设若再走这3990米,早已力之不支了。就是习惯了登山的我,如果不是下榻蒙山会馆,当天上下,再走木道,恐怕也是比较困难的了。
但此行我毕竟拥有了独走木道的幸福。早已厌倦了城市的喧嚣,人事的纷争,现在于这个几乎是独属于自己的静寂世界里,真真正正地感受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从容与淡然。
走至木道最高处时,方知我是从北路而上的,意欲领略它的全程之美,当然要从南路而下了。越往下走,红松圆木道上就越失去了原始的状态,有的已经显出人行磨擦的光亮。显然,在距离蒙山会馆较近的路上,已有不少游人踏过。看来,真正走完它的全程者并不太多。
看到蒙山会馆时,已是6点多钟。回首走过的木道,还是依依不舍。明天一定早起再走木道;以后再游蒙山,也一定重上木道。
白天有了独游木道的兴致,夜间的蒙山也定别有情趣。
晚上9点多钟,在我房间谈话的朋友一走,我便立即走出蒙山会馆。宾馆之外漆黑一片,就是绿色,也全部溶化在茫茫夜色之中。借着宾馆门内的灯光,门外三四十米的地方还可以供我缓步而行。
空气如白天般清新,夜间则更加静谧,除几声虫子的低声弹唱之外,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。这份幽静,数十年已经没有感受过了。而心灵的恬静,也如这夜一样,不知不觉地融入到自然的神秘里。
偶尔抬头望天,原有的心理平静旋即为惊讶之心替代,因为只有在儿时所见的满天星斗,现在突然重现在我的视野之中。银河横亘天际,密密麻麻的星星躺在“河”中静静地听着牛郎织女委婉的诉唱。银河之外也是星光灿烂,洒满天涯,与黝黝的山林,形成鲜明的比照。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,一个在城市绝对看不到的世界。突然想到,古代的隐者终老山林而不悔,会不会是在留恋闹世间不见的幽静与绚丽。在延年益寿之时,他们更在追索一种心灵的纯净,思想的超然。这比那些在仕途中奔波行走者,心里永远装载着一道怡然而乐的风景。
星斗如此灿烂,自然如此神秘,人生如此短暂。属于自己的那份淡然那份自然,真的是可欲而不可求吗?
(《行旅有道》,陶继新 著, 2015年10月第1版。)